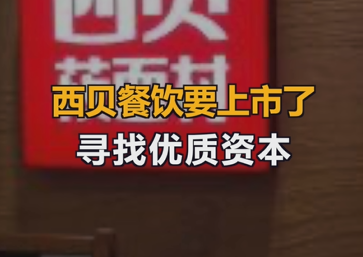风雨兼程 市场追梦——记创业广发证券点滴事
■ 原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陈云贤*
2020年10月中旬,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广东大地激荡起阵阵春潮。“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时代强音,让我由衷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而自豪。恰在此时,中国证券业协会的一纸约稿函,又让我的思绪穿越30年的风雨,回想起中国资本市场源流之始的许多人、许多事……
一、我不是下海
1990年底,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开市鸣锣,余音绕梁之际,首批证券经营机构已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北京成立,在洋溢着全新气象的21世纪饭店,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作为广东发展银行证券部的代表,我很荣幸地出席了这次富有开创意义的全国性行业盛会。
彼时彼刻,尤感幸运的是,广东发展银行证券部不久前刚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领取批文,即将筹建完成;而我本人,则刚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一个多月,在中国证券业协会首次会员大会召开之前,我刚刚实现了从资本市场理论研究者向证券经营机构管理者的身份转变。
1991年9月8日,在广州市海珠广场的一处柜台前,广东发展银行证券部正式挂牌营业,我担任总经理。包括我在内的员工仅有6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现金仅有200万元。作为证券行业首批经营机构,广发证券在筚路蓝缕中开启了征程。
初创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一片充满魅力的蓝海,每一家证券公司既享有发展的机遇,也承担着未知的风险。而在当时的我看来,资本市场并不是完全未知的,其发展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份自信,源于此前三年我在北京大学的求学和研究经历。
1988年初,我还是福州大学财经学院的一名讲师,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我经历过“上山下乡”,在贫瘠的农村插过队,对“知识改变命运”有着深深的憧憬。继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在著名经济学家陈征先生门下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我继续一边工作一边备考,终于在1988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萧灼基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专家之一,他带领我们一众学生,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在经济学界领风气之先。在他的鼓励下,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确定为一个前沿课题:比较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金融体系,探索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模式。于是,在中国资本市场正式成立之前,我已走进资本市场学术研究的大门,潜心研究这一前沿领域的内在规律。
该课题的“前沿”也意味着研究道路的艰辛,国内能够借鉴参考的资料十分稀少,理论上的瓶颈重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内理论界,对资本市场姓“社”姓“资”尚在争议中,将其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我内心深知,要冒着不能如期毕业的风险。
在北大宽容自由的学风下,萧灼基教授鼓励我们跨越门第,向其他经济学家请教问题。陈振汉、胡代光、范家骧、张友仁、厉以宁、刘方棫等一批经济学教授先后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宝贵指导。尤其是在陈岱孙先生、萧灼基教授的分析和鼓励下,我大胆地将资本的要素纳入生产要素当中,在国内理论界中实现了突破。1991年,我的博士论文《中外证券投资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同年8月,该论文经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整理,以《证券投资论》的书名正式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研究证券投资理论的著作。
这段求学与研究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学术研究虽然艰辛,但“无限风光在险峰”,理论王国中的每一步探索前行,都令我深深着迷。萧灼基教授和一大批名师的风范,更如春风化雨般沁入我们晚辈学人的心田。身为学生的时光虽然有限,但毕业之后,学术理论仍是我矢志不渝的追求,知识分子的品行操守仍是我坚守一生的底色。
1991年的春天,面临毕业后的不同选择时,我决心南下来到广东发展银行,受命筹建证券部。做出这一选择的首要考量,是因为在我看来,改革前沿阵地的广州和虎虎有生气的广东发展银行,是我能够将资本市场理论研究付诸实践的优质“试验田”。在新生的中国资本市场创建广发证券、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值得托付个人命运的美好事业。
幸运的是,在资本市场的知行之路上,我并非独行。广发证券起步时家底微薄,但在伍池新行长等领导的开明支持下,我不仅得到了所在银行系统内专业人才的扶助,而且努力从经济理论学界网罗了一批高层次人才。中央党校教授、与我相识于1985年的挚友马庆泉博士,听说我在广州创办广发证券后,欣然南下,成为我最亲密的创业伙伴。我的硕士同学、当时已成为福州市最早几位博士之一的方加春博士,在我的多次力邀之下,放弃稳定的事业平台,举家迁来广州,投身广发证券。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的开门弟子、与我相识多年的李建勇博士,也在我长达数年的诚邀之下,作别他在西南财大的事业,从经济理论界知名学者转身成为广发证券干将,等等。
广发证券的创业条件艰苦,马庆泉博士甚至三四年在办公室睡地铺,但是受到创业精神感召的一批博士,以及王鸿茂、叶俊英、李纾之、董正青等一大批硕士、学士和专业人才,成为广发证券最宝贵的资源。“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广发证券多个业务条线成长迅速,1995年开始进入全国十大券商行列。1996年初,广发证券已拥有17名博士,在当时的证券行业十分罕见。这一现象受到社会媒体的关注,1996年5月27日,华南权威媒体南方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报道《资本市场上的“博士军团”——来自广发证券公司的报告》,“博士军团”自此成为多年来广发证券最具标志性的专有名片。
这段时期,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媒体采访,是新华社驻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他先后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分别向我和马博士发问:“你们下海主要是怎么想的?”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和马博士此前并无沟通,但心有灵犀,在第一时间都做出了相同的回答:“我们不是下海。”
我否认“下海”这一说法,是因为创业多年后,虽然挂着“董事长”等头衔,但内心深处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一直没有变。我始终认为,广发证券是一个事业平台,是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托付报国情怀、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中国资本市场实践的地方。马博士的回答则更具激情:“我们不是下海,我们是‘北伐’,要在广州打造一个金融集团,向北方、向全国进军。”
我对“下海”的说法甚至有一些本能的排斥,隐约感到这关乎个人的金钱观。身处资本市场,并不应讳言金钱,广发证券在具有一定规模后,对员工的物质待遇也有市场化的提升——但是,金钱与物质既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应成为事业发展、团队成长的唯一动力源泉。
那么,作为一个事业平台,广发证券发展的动力源泉应当是什么?在创业经历中,我们的阻力乃至风险是什么?至今回想,我感受颇多。
二、事业,行走在悬崖边缘上
伴随着市场的潮涨潮落,中国证券业步入1995年时,经受了第一次显著的浪潮冲击。许多曾经出席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的证券经营机构,由于此前扩张失速,在这一年遭遇了经营困境。“327”国债事件进一步催化了行业局势,曾经令人仰望的大型券商在这一年发生了更迭,过早地从行业中消失。
遗憾之余,更觉资本市场的多变与无情。在此前一年,广发证券已由原来的证券部组建为专业的证券公司,思路清晰地按照广义的投资银行模式来经营。公司内部提出了“股份化、集团化、国际化、规范化”的发展目标,成为坚持多年的“四化”创业纲领。1995年的广发证券,抓住银证分业与行业逆周期的契机,通过自设、系统内整编和市场化并购,网点规模和资本实力显著增强,投资银行业务更通过一系列标杆项目打响了名号,业务领域从广东迈向全国。
1995年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两件事:其一,在组织的高度信任下,我成为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项目在执行层面的牵头人。我与4名员工前往北京封闭办公整整3个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直接监督下,推进处理了十分繁杂的业务、会计、法律和综合事务,为这一重大而敏感的项目贡献了心力。其二,是我的身体状况频频亮起红灯。在组建公司前后,熬夜加班多,精神压力大,我经常感觉到身体不适,但除了虚胖,却又检查不出来问题,而当时的医学并没有“亚健康”的说法。直到这一年,我因为心脏难受直接住院,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神经科的一位老医生十分严肃地告诉我:虽然你年龄还不到40岁,身体看似没有什么毛病,但是身体状态已经像是60多岁的老人,出现了老年人身上才有的许多症状。
在这个激情的创业年代,一颗事业心,一副健康的身体,似乎很难兼得。记得在公司成功改组并举行庆典的那天,中顾委委员、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欣然为广东广发证券公司题字“如日方升”。幸如任仲夷同志所愿,公司的事业呈现了很好的发展势头,但包括我在内的多位班子成员,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证券行业是典型的高强度脑力行业,日常的管理经营已不轻松,如果对学习研究有所追求,以及每当诸如对外收购项目、发行上市业务的机遇来临时,要全力争取,就难免心力交瘁。包括广发在内的许多证券公司,干部队伍中都发生过令人喟叹的极端事件。也许,一个人只要有了事业心,就如同行走在悬崖边缘,这第一道悬崖,就是个人的健康。
证券行业早期的草莽特性,则在无形中垒起了第二道悬崖,这一时期证券机构的经营者往往行走在法纪与规则的边缘。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证券公司大多有着难以遏制的扩张冲动。一方面是因为行业规模尚小,证券公司资本金匮乏,且没有稳定的盈利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证券法规和监管不够完善。种种因素交织之下,证券公司的投资业务以及拆借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等成为行业的灰色地带。当时实力雄厚的龙头券商甚至拿出数十亿元的重资,在天津进行主营业务以外的拆借交易。而随着法规与监管逐步建立健全,证券公司大多难以从此前的灰色地带全身而退,成为“以新规则衡量旧行为”的牺牲品。
也是在1995年,随着行业经营乱象的增多,中央政府相关部委组成了多个调查组,分赴各地检查。广发证券在一年中先后迎接了7个批次的调查组,总部所在地广州华泰宾馆16楼格外忙碌。漫长的调查过后,广发证券在武汉交易市场的200多万元资金被审计出问题,但是,这一额度风险可控,公司经营总体上是规范的。应当说,广发证券审慎规范的经营理念以及在业内率先自设稽核部、加强内控监督等举措,是我们能够避开“规则陷阱”、能够从这第二道悬崖边缘走过的重要因素。
第三道悬崖,是钱财的诱惑。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尤其是中高层干部,手中掌握的财权远大于社会多数行业。权力大,风险大,悬崖边缘的考验比比皆是,证券行业成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犯罪的多发地。从1992年造成恶劣影响的深圳“810事件”开始,证券市场乱象就与内部腐败、个人私欲纠葛不清。曾经的信托巨头中银信托在1995年轰然倒地,我和广发的同事们在接管时发现,其负责人的违法乱纪、干部队伍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这种类似的发现,在广发证券历次重大托管、收购工作中屡见不鲜。所以,员工队伍尤其是管理干部的金钱观,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对事业的雄心抱负与对个人物质利益的需求,决不能混为一谈。更进一步地说,正是因为公私分明,我们才更敢于做决策、推改革、创事业。在1995年的7批次调查中,广发证券能够经得起各部门的轮番考验,除了公司管理总体规范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司所有的经营决策无一牵扯班子成员的个人利益问题。
与钱财这道悬崖伴生的,还有酒色问题。在早期证券公司跑马圈地式的业务开拓中,营销、公关都是相互比拼的战场。在许多地方的风土人情里,不喝酒的确很难做成业务。但如果沉湎于此,甚至以业务和管理为借口而自我放纵,则贻害无穷。相关区域的同业就有前车之鉴。广发证券在任命异地赴任的营业部负责人时,我都会单独谈话,除了谈工作,还重点告诫两个方面——钱财和酒色。至今,这些干部相聚聊天时,许多人仍记得我要求的“静、清、勤、谨”四个字。这是我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习性对广发干部生活纪律做出的要求。
最后一道悬崖边缘,是理想信念的边缘,对于公司平台,对于管理者个人,都是如此。21世纪之初,适逢广发证券成立十周年,公司梳理了“知识图强、求实奉献”的价值观,也审视了创业阶段的发展动源。其中,“规模动源”“利益动源”“机制动源”是外在动源;“知识动源”“协同动源”“使命动源”是内在动源。外在动源是有一定限度的,是可能减弱的;内在动源是无穷的,是公司存在发展的真正力量所在。我们向员工倡导,对个人事业、对公司发展、对国家和社会兴亡,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世纪之交,许多证券公司在增资改制中蜕变,广发证券坚持了自立自强的发展道路,即使遭遇了风雨,但这份信念一直长期坚守。
从1991年到2003年,我在广发证券工作了12年。12年既漫长,又短暂。值得欣慰的是,广发证券创业有成,成为具有较好影响力的证券公司,而且我们共同创业的一批人,在这12年间从一道道悬崖的边缘走过,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资本市场的浪潮起伏,对身处其中的个人命运也造成了深刻影响。回首30年,站在2020年的时点,在相同的时间长度中,从行业初创期走过来的证券公司领军者们,阅历与感受各不相同。细细想来,在祝福之余,仍感慨万千。
三、能够留给社会和历史的,更多的是精神财富的东西
2019年,作为中国证券期货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证券博物馆专门向广发证券征集创业期的史料。于是,我从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退休后,再次走进了中国证券博物馆所在的上海市黄浦路浦江饭店,在这个中国资本市场源流之地,向博物馆捐赠了一批学术著作和实物展品。
所捐赠的学术著作,是我和马庆泉博士、方加春博士、李建勇博士、肖成博士、汪良忠博士和姚汝信博士等人的作品,是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知行之路上的心血之作。其中,我捐赠的《证券投资论》《投资银行论》和《风险收益对应论》,分别于1991年、1995年和1998年正式出版,是我在创业广发证券过程中,对资本市场连续深入的、自成体系的理论思考。
《风险收益对应论》中特别强调了一个论述:投资银行要将自营投资的资金规模控制在总资产规模的5%以内。直到12年以后,即2010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法案中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要求:在自营交易方面,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资本的3%。这一要求其实并未突破1998年《风险收益对应论》提出的理论框架。所以,广发证券“麻雀虽小”,却一样能够实践出真知,而且是“领先时代的真知”。从管理经营中来,到管理经营中去,这些理论思考也曾帮助创业期的广发证券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知行合一”。例如,在1999年前后的股市中,券商代客理财盛行,但广发证券经营班子结合风险收益对应论,作出了不涉足这项业务的决策,躲过了后来的市场危机。
我还记得,当年在准备将《风险收益对应论》正式发表前,曾遭到广发证券一些同志的反对。因为著作中的许多经验和数据,来自广发证券的实践,换言之,广发证券为它们交过学费。但我还是坚持认为,知识应当是属于社会的,将广发证券探索的经验公开发表,只要能够为行业带来启发,就是可贵的贡献,这种精神财富的贡献,并不亚于广发证券规模与利润的贡献。
这种对行业精神财富的倾注,在创业广发过程中其实还有很多。例如,1991年刚南下广州时,我骑着自行车,对当时的广州证券行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形成了三篇《广东发展银行证券业务设想》,向行领导正式汇报;又在三篇报告的基础上,从广东省证券业整体发展的角度,形成了另一篇正式报告《发展广东证券市场的设想》,提出了股债并举,一、二级市场并存,国内外市场并用等建议。再者,2000年9月至2001年9月,我赴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学习,归国时撰写了《美国金融体系考察研究》一书,并在这本专著的基础上,用心撰文思考了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证券公司将面临的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要做好对应的六个准备。“六大挑战”和“六个准备”得到了中国证券报的重视,其在经过整理后以内参的方式报告给国务院主要领导。据后来的反馈,国务院主要领导对该期内参作出了批示,文件转至全国副部级以上干部传阅。
受求学经历的影响,不管岗位如何转换,我始终对读书、写书、教书怀有深深的情结。在佛山市和广东省工作期间,我写下《超前引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中国金融改革发展探索》等著作。退休以后,我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9所高校为研究生讲授《中观经济学》《国家金融学》等新课程。2020年,即使受疫情影响,也想办法通过网课的方式继续讲学。与年轻的学子在一起,我由衷地感到快乐。
细细回顾这些经历,并非为了自诩所谓的功劳,而是认为,作为改革开放时代洪流中的一名知识分子,能够留给社会和历史的,更多的是精神财富的东西。在1991年,我有幸从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踏入了行业的源流,三十年风雨兼程,追寻着广发梦、金融梦、中国梦。知识的追求、积累与传播,正是我们回馈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最好方式。相信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下一个三十年走向更辉煌、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