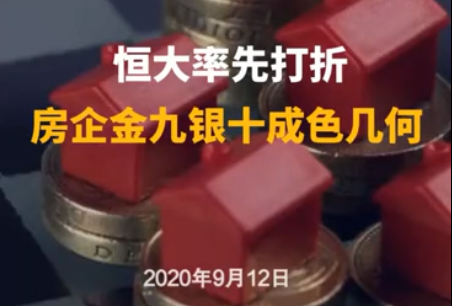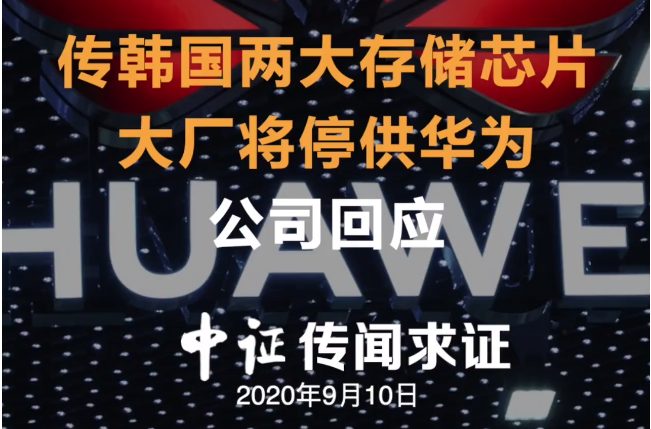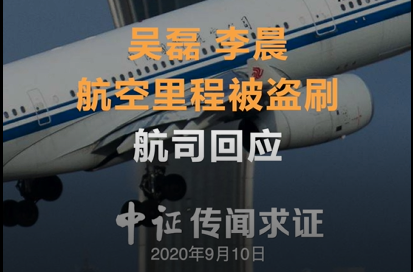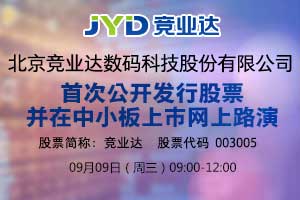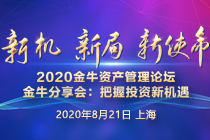博弈进行时:航空公司“抢飞”北京新老机场
“纠结”的三大航
通知透露的另一大重磅信息是,东航和南航将作为新机场的基地航司,并按照各承担40%旅客量的规模规划发展。
40%的旅客量设定主要是为了鼓励东航和南航进行整体搬迁。客观来说,航司从首都机场搬至新机场,在北京的业务开展将会受到巨大影响,东航和南航更是首当其冲。
东航在北京市场的地位虽不如基地航司国航,但在京沪航线上,东航的市场份额超过了50%。作为连接两大“超级”市场的航线,京沪线是国内航线中的黄金航线,一直拥有极高的客座率。撤至新机场,东航不得不面临旅客流向其它航司的风险。
东航显然不会愿意离开首都机场。据悉,东航早期有意将中联航迁入新机场,自己留在首都机场T2航站楼。对东航而言,这个方案“完美”但过于“天真”。不过,中联航的基地倒是在南苑机场,根据规划,的确要迁往新机场。
另一边厢,南航在北京-广州航线上也面临着类似的风险,不过与东航相比影响要小一些。事实上,南航向来重视北京航线,但一直受制于在首都机场的发展空间,新机场项目初期,南航很快就确定要全面搬迁至新机场,借力新机场打造上海与北京“双枢纽”也是南航至今津津乐道的议题。
新机场的一大劣势在于距离市区更远,交通接驳也存在不确定性。从上海来看,尽管浦东机场已经有地铁、磁悬浮、机场大巴等多种公共交通运输工具进行接驳,但航空公司开通国内航线时一直都更倾向于飞虹桥机场。
“从历史经验上看,地理位置在民航领域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于占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东航在浦东机场运营京沪航线的初期,就不得不下调20%的价格来稳定客源。他推测,南航和东航转场至新机场后,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境况。
一位接近三大航的业内人士还提出,新机场的航站楼构型及其形成的港湾效率也不是完全令航司满意:飞机如果在两个最远指廊间通行,直线距离太远,而且可能会“堵车”。对此,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司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仿真模拟中,目前的设计可以将延误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相差一刻钟以内的航班都足以消化。”他说。
为了“拉拢”东航、南航在新机场运营,民航局为两个基地航司提供了一系列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记者从两份文件中看到,这些优惠包括免收新机场始发航班民航发展基金、对起降费等常规费用提供折扣、降低飞机税费、对基地项目资本金部分的融资利息予以补贴等。
与东航、南航等天合联盟成员相比,星空联盟成员能够留守首都机场,短期内可以“放一百个心”。以国航为例,它将在占据T3最大份额的基础上,再承接一大份空闲资源,巩固在首都机场的枢纽地位。“国航一直定位于洲际性的枢纽航司,但长期受制于首都机场的时刻,这下终于有了大施拳脚的机会。”于占福说。
但国航却对此尚有疑虑。国航一位内部人士在评价国航留守时,曾用过“短多长空”四个字,长期来看留在首都机场的利弊仍然存在变数。
“新机场从规划建设的水平来说还是要比首都机场好很多,未来磨合好了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都会得到提升,而首都机场既有的问题都已经是已知的了,未来优化空间不大。”这位人士表示。
客观上说,新机场和老机场各有千秋,也各有隐忧,把运力全部投放在一个机场,显然不是航空公司的最佳配置方式。
有意思的是,国航和南航都在今年成立了“新”航司:国航旗下原公务机航空北京航转为民航公司,而南航则更是抢占先机注册了“雄安航空”。在双方都对分配方案不甚满意的情况下,业内多将此解读为在另一个机场的“占坑”利器:北京航进入新机场,雄安航进入首都机场。
不过,三大航旗下航司能否进入另一方机场尚未有明确的解释。最早期的思路中,中联航和北京航就明确被标注为东航和国航旗下公司,一同建设基地,但是规划对众多子公司却未一一提及,这也给了三大航更多“谈判”的空间。